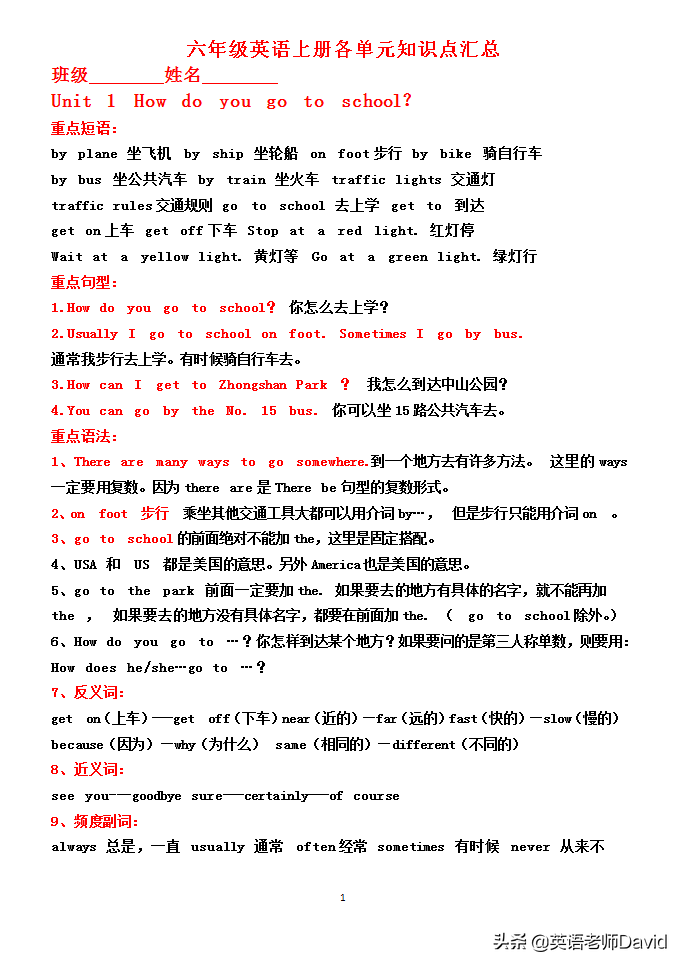北京晚报·五色土 | 作者 黄逸
尔来十五年,残虏尚游魂。
遗民沦左衽,何由雪烦冤。
这是诗人陆游在《感兴二首》中的句子。将“左衽”视为“受异族统治”的象征,是南宋时常用写法,比如陈与义的“丧乱哪堪说,干戈竟未休。公卿危左衽,江汉故东流”。再如胡铨在《戊午上高宗封事》中写道:“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,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!陛下一屈膝,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,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。”

大同北魏彩绘乐俑
中原服装从来是左衽、右衽均可,所谓胡人“披发左衽”,或丧服左衽,虽出自经典,但从考古看,绝非通例。
陆游等反感左衽,是特殊时期的激愤之语,一方面是自唐末起,中原王朝有“排胡”倾向,这种心态长期延续;另一方面是遭遇亡国之痛,错误地寄情于旧服。
令人惊讶的是,左衽、右衽这种不靠谱的说法近日再起波澜,因迪士尼角色玲娜贝儿玩具的中秋服(其实不是汉服)是左衽,被网友批为“丧服”,是“辱华”,实属贻笑大方。
首先,热爱传统文化是好事,但不深入了解,乱怼一气,好事就成了坏事。
其次,不应把地方知识当成普遍知识,要求别人也熟知。
第三,了解不多便急于卖弄,动辄恶猜,有失涵养。
第四,特殊时期的误会,不应当成真理。
关于左衽、右衽的辨析,前人成果汗牛充栋,至今误会流传,可见科普之难。
古人只说了“三句话”
“汉服”之说,不早于汉武帝后期。《史记》中,贰师将军李广利征西域遇挫,与部将赵始成、李哆等人商量暂驻西域宛城,称:“闻宛城中新得秦人,知穿井,而其内食尚多。”可见,此时中原人仍自称“秦人”,服装应也是“秦服”。
为讨论方便,本文将商代中期以后,至民国时期的中原服装,统称为“汉服”。
在先秦文献中,只有三条涉及左衽。
一是《论语·宪问》中记孔子的话:“管仲相桓公,霸诸侯,一匡天下,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,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”意思是没有管仲,我们早被夷狄征服了,如今只能“被发左衽”。“被发”一般认为是披散头发,而不像中原那样戴冠。“左衽”一般认为是左边衣襟压住右边衣襟,这被认为是胡人的穿衣习惯。朱熹便注为:“被发左衽,夷狄之俗也。”
二是《礼记·丧大记》:“小敛大敛,祭服不倒。皆左衽,结绞不纽。”孔颖达解释说,中原服装右衽,因左手解带子比较方便,但逝者的丧服左衽,表示不用再解带子了。
三是《尚书·毕命》:“四夷左衽,罔不咸赖,予小子永膺多福。”意思是四方的蛮夷都不值得信赖,但《毕命》已确认是后人伪造的,不论。
记录如此少,作为后人“中原右衽,夷狄左衽”“活人右衽,逝者左衽”的论据,显然不够。
其一,从甲骨文看,商代已有左衽、右衽之分,与《论语》《礼记》成书时间相距甚远,两书未必确知其渊源。
其二,两书只是随口一提,未必是定论,后人有过度注释之嫌,且未拿出依据。
汉画像石上左衽更多见
更大的问题是,文字记录与考古结果严重不符。大量出土文物证明,古代中原服装不分左衽、右衽,周边夷狄的服装亦如此。
从先秦到汉代墓葬中的石刻、铜雕、图画中,左衽与右衽均有。比如:
河南安阳殷商墓葬中出土的玉人,右衽。
四川“三星堆”出土“大立人”,左衽。(也有学者认为是左袒,即左边光膀子)
辽宁西丰县西岔口汉代墓葬,两武士牌,一左衽,一敞怀。
山西侯马东周男女人物陶范,均左衽。
河南洛阳金村战国巫女玉雕,均右衽。
徐州北洞山西汉墓男俑,有左衽。
在汉画像石中,左衽更多见,东王公、西王母、伏羲、女娲、日神、月神、羽人等都是左衽,侍者、武士、门吏等也常左衽。甚至在同一图案中,有的是左衽,有的是右衽。有学者认为,左衽、右衽可能没有特殊含义,只求对称——图左人物画成右衽,图右人物画成左衽。
坊间传言称,右衽与左衽来自劳动。中原重农耕,右衽时,右手可方便将小工具存放在怀中,而游牧民族多左手持马缰、右手拿武器,左衽便于左手入怀取东西,且左胸多一层布,能保护心脏。
这些说法与朱熹的注一样,都是“合理推断”,人类中10%是左撇子,这该怎么办?此外,游牧与中原都是多民族构成的,游牧人群也有农耕,中原民族亦乘马,这些“功能性”设计岂不适得其反?
此外,古人服装设计与礼制关系密切,不以实用为本。从甲骨文、金文看,“衣”的字形即衣襟叠压,有时偏左,有时偏右,说明此时左衽与右衽没有严格区别。
汉代对胡风持开放态度
那么,孔子说错了?
孔子可能也没错,当时中原战乱,只能夸大华夏共同体意识,所谓“夷狄之有君,不如诸夏之亡也”,将右衽、着冠等也转化为身份象征。不仅孔子如此,《左传》也写道:“我诸戎饮食衣服,不与华同,贽币不通,言语不达。”体现出在特定时期顾影自怜的心态。
汉代则军事强大,压制了北方匈奴。1993年,江苏省尹湾汉墓出土《武库永始二年兵器集簿》,记录东海郡武库状况:弩机53.8万件、1145.8万支弩箭,7.75万张弓和120万支箭,14.3万套皮甲,近10万把剑和2.5万口刀,兵车7000多乘……一郡且如此,全国战力堪称恐怖。
汉代对胡风文化持开放态度,丝绸之路开通后,汉朝派往西域的“使者相望于道,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,少者百余人……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,少者五六辈,远者八九岁,近者数岁而反”。
汉武帝时,“西域献吉光裘(光亮毛皮制成的裘服),入水不濡,上时服此裘以听朝”,汉灵帝时,“好胡服、胡帐、胡床、胡座、胡饭、胡箜篌、胡笛、胡舞,京都贵戚竞为之”。
东汉时,大量胡人内迁,到公元3世纪,关中100多万人口中,胡族约占一半。山东、陕西、河南、四川等地出土的东汉神仙图像多左衽。文化自信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,孔子时条件不行,所以纠缠细节,汉儒则心态平和、大而化之,坚守华夷平等,即“中国之与边境,犹肢体与腹心也”,主张“畏其威而从其化,怀其德而归其境”“附远宁静,怀来万邦”,反对开疆拓土、妄起战端。
唐从“尚胡俗”到“排胡”
孔子眼中的“大问题”,在汉儒看来是可有可无的“小问题”。此后三国魏晋南北朝,包括唐代初期,左衽、右衽虽常被提起,但未引起太大反响。
一方面,唐朝君主有鲜卑血统,尚胡俗;
另一方面,魏晋南北朝期间中原混战,北方尽被胡尘,世风已变。北宋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记:“中国衣冠,自北齐以来,乃全用胡服。窄袖绯绿,短衣,长靿靴,有蹀躞带,皆胡服也。窄袖利于驰射,短衣长靿,皆便于涉草。胡人乐茂草,常寝处其间,予使北时皆见之,虽王庭亦在深荐中。予至胡庭日,新雨过,涉草,衣裤皆濡,唯胡人都无所沾。”
唐朝初期对胡风同样持开放态度。“慕胡俗、施胡妆、着胡服、用胡器、进胡食、好胡乐、喜胡舞、迷胡戏,胡风流行朝野,弥漫天下”,可“安史之乱”后,唐朝态度大变,转向“排胡”。据《新唐书》,唐朝共369名宰相,胡人所占比例不足7%,且多在唐初,如宰相长孙无忌、于志宁、宇文士及、宇文杰、豆卢钦望等。
唐宣宗时,白敏中(白居易的堂弟)拜相,同时有毕諴、曹确、罗劭权,可能都有胡族血统,宰相崔慎猷立刻辞职,称:“我该回家了,如今担任中书令的,都是蕃邦的人。”
唐文宗时,郑覃任宰相,他重提左衽、右衽,说:“晋武帝以采择之失,中原化为左衽;陛下以为殷鉴,放去攸宜。”意思是晋武帝当年误把中原服制改成左衽,不久亡国,您不能忘了历史教训啊。
“排胡”运动的后果是,华夷之辨再被夸大,北方胡人渐少,多去南方发展。
左衽、右衽非华夷标尺
“排胡”之风延至宋代,而北方最大威胁契丹左衽,宋政和七年(公元1117年)下诏:“敢为契丹服,若氈笠者、钓塾者,以违御笔论。”钓塾即袜裤,妇人之服。可宋徽宗时,京城处处歌蕃曲、用蕃物。
契丹百姓也喜欢中原风格,北宋重臣韩琦记:“契丹宅大漠,跨辽东……至于典章文物、饮食服玩之盛,尽习汉风。”乾亨年间(979-982年),契丹改革服制,三品以上北班官员行大礼必着汉服。1055年,所有官员典礼时均穿汉服。
北宋灭亡后,南宋学者吕中竟认为,幽云未收回,皆因“中国之民陷于左衽”,创深痛剧,人易失理性。
学者董晓荣钩沉,蒙古人初期袍服与突厥人同,均左衽,宋代时成右衽。宋人彭大雅在《黑鞑事略》中记:“其服,右衽而方领,旧以毡毳革,新以紵丝金线,色以红紫绀绿,纹以日月龙凤,无贵贱等差。”
1253年至1255年见到蒙古的法国人鲁布鲁克说:“这种长袍在前面开口,在右边扣扣子。在这件事上,鞑靼人同突厥人不同,因为突厥人的长袍子在左边扣扣子。”
贵由汗时代曾到蒙古的意大利人加宾尼说:“第一天他们都穿白天鹅绒的衣服,第二天……那一天贵由到帐幕穿红天鹅绒衣服。”元朝公务礼服是质孙服,右衽,此时已制度化,每天换一种颜色,且全体统一。据《元史·舆服志》:“质孙,汉言一色衣也,内庭大宴则服之……下至于乐士,皆有其服。精粗之制,上下之别,虽不同,总谓之质孙云。”
极少量质孙左衽,在小范围内使用。左衽、右衽绝非别华夷的标尺。
大可不必强做解人
明代朝鲜使臣常从海路来中原朝贡,留下《朝天录》,据1623年7月至1624年4月来华的赵濈记:“女子且有左衽者,岂齐鲁遗风有左衽之俗耶?怪哉怪哉!”赵濈精通儒家典籍,自然知道左衽是丧服或胡服,而山东又是圣人之乡,岂能不知此礼?
学者刘宝全、邵双双在《朝鲜使臣中的明末山东社会风俗》一文中指出,朱元璋登基后,大搞“去元化运动”,“诏复衣冠如唐制”,可唐朝服制有很多来自北方胡服,并不是什么“正统的中原文化”。上面懵懂,下面只好乱穿。
朝鲜另一位使者崔溥在《飘海录》中,也说中国江南“妇女所服,皆左衽”,江北则“自沧州以北,女服之衽,或左或右。至通州以后,皆右衽”。
中国是大国,地域文化丰富多彩,除非极端强制,不太可能全民都左衽,或全民都右衽,自古都是各从其便,偏偏一些别有情怀的人,总想把这些生活细节统一化,以创造共同的身份感,目的是以寡御众,但鲜有成功者。
后人不明其理,强做解人。有人甚至称,中原自古右衽,左衽是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的副产品,其实“胡服骑射”改造的是下裳,当时裤无裆,需外罩深衣,无法骑马,赵武灵王将游牧民族的裤子引入中原,和左衽、右衽无关。
左衽、右衽是非常小的事,即使说错了、用错了,也不必口出恶言,何况人家原本没错。这种过于狭隘、锱铢必较、绝不宽容的精神,难免落入吕中式的误区,拿非理性当解决方案。可吕中忧国忧民,比懂得少还要卖弄,要强得多。(责编:沈沣)